影评:《小小的我》,大大的世界
作者:培声听力语言中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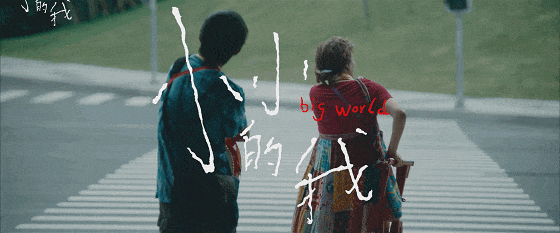
聚焦脑瘫人群生活的电影《小小的我》近期上映,引发大众对于脑瘫群体的广泛关注。
现实生活中,脑瘫患者的语言和语音能力往往受到多重限制。由于认知障碍、口腔肌肉的无力或协调性不足、呼吸控制困难等因素,许多脑瘫患者面临语言理解和表达困难、语速过快或过慢、发音模糊等问题,这些问题往往导致他们在社交、学习和生活中面临巨大挑战,甚至被误解或忽视。
十余年来,培声致力于通过科学循证的训练方法,帮助沟通障碍的宝贝们更有效地沟通、更自信地表达。我们的每一位小小患者都像一束光,照进我们的诊室,照亮我们的生活。
希望通过像《小小的我》这样温暖而真实的作品,唤起社会对脑瘫患者等特殊群体语言康复需求的关注。我们相信,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聆听,每一个生命都可以通过语言绽放光芒。让我们一起,为更多人点亮希望的未来!

微光之下,沉默的大多数
《小小的我》并不是一部让人痛哭流涕的苦情电影,它更像是一束温暖的光,照向那些常常被忽略的生命。通过刘春和,这个生活在身体牢笼中的脑瘫青年,电影抛开了对“残疾”的标签化凝视,而是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完整的、复杂的人所拥有的情感、欲望和挣扎。
刘春和是中国600多万脑瘫患者的缩影,但电影让他成为“他自己”。他有独立的想法、执拗的追求,有被现实撕扯的痛苦,也有偶尔得以喘息的微小幸福。片中没有用惨烈的冲突来刺激观众的同情,而是用一种近乎日常的方式,讲述刘春和如何用颤抖的手指捡起生活的碎片,拼成一幅属于自己的图景。
电影的力量在于其克制的叙事。外婆的支持、母亲的焦虑、雅雅的靠近与离开,构成了一种张力。每一段关系都没有非黑即白的简单化,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中背负着难以言说的重负。这种真实感让观众意识到,刘春和的故事不是特例,而是这个社会中沉默的“大多数”的缩影。


没有翅膀的飞翔
电影最动人的部分,是它如何赋予一个脆弱的身体以飞翔的力量。刘春和的每一次努力——无论是穿过熙攘的街道应聘咖啡店,还是在众目睽睽下大声背出相声贯口,抑或是对雅雅说出的那句“我想喜欢你”——都像是一次没有翅膀的起飞。这些努力或许看似微不足道,但却让刘春和证明:他不是生活的附属品,不是疾病的牺牲品,他有能力塑造自己的存在。
尤其是那段与外婆一起学习打鼓的情节,既充满了生活的诗意,也体现了人类独特的相互扶持能力。刘春和在鼓点中感受到了节奏与力量,而观众则在那一刻感受到:即便是最深的孤独,也可以因为被需要而拥有意义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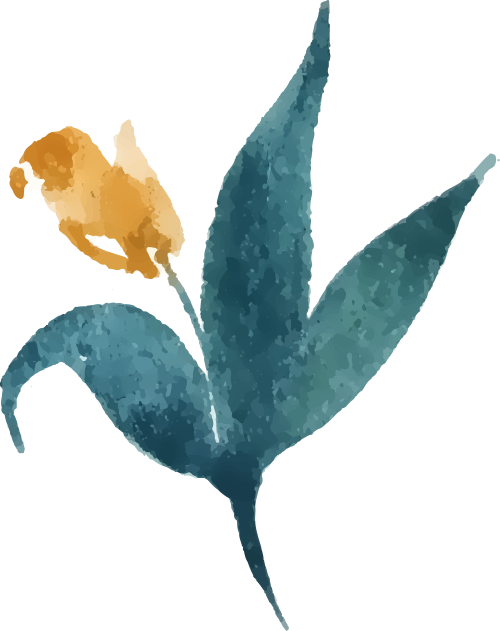
给隐形的群体一个容身之所
《小小的我》不仅为脑瘫患者发声,更将镜头对准了社会的多个边缘人群。退休的老人、社会中的弱势劳动者、甚至像雅雅这样暂时失落的年轻人——他们都在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那些隐形的悲欢,都被电影温柔地呈现了出来。
编剧游晓颖提到,在她母亲参加的老年合唱团中,有一位外婆总是带着唐氏综合征的外孙参加活动。这一真实经历成为电影剧本的原型,但选择以婆孙作为叙事中心,不止于单纯的生活还原,更包含了一层深刻的社会表达:残疾人和老人看似因“政治正确”被摆在了优待的位置上,但他们的真实需求与个体价值却往往未被真正看见。


平视与尊重:不只是“看见”
电影的一大突破,是它不止停留在“呼吁关注”的层面,而是真正从尊重的角度来描绘刘春和的生活。观众并不只是因为他的病痛而怜悯他,而是被他对尊严的渴望和执着所感染。
刘春和说:“我在人群里,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,有怜悯我的,有害怕我的,有憎恶我的……可是很少有一种眼神,是敢于直视我的,拿我当做自己人的 。”这种渴望不是仅仅为了“被看见”,而是希望被真正地接纳。这一层需求,也是我们在面对残障人士时最容易忽略的部分。


每一个“小小的我”,
都应拥有“大大的世界”
电影的最后,刘春和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他兴奋地举起那张红色的纸——这一温情的结局表达了主创对未来的乐观期待。而对于观众而言,或许,从直视刘春和的眼睛开始,就有什么已经在改变了。
《小小的我》呼唤我们直视每一个被忽视的生命。它告诉我们,尊重不仅是施舍和怜悯,而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每一个微小的个体,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脑瘫患者的杰出故事从不鲜见:无论是用诗歌诉说生命复杂性的诗人余秀华,凭幽默撕开偏见的脱口秀演员小佳,还是用科学、艺术或运动突破自我的克里斯·福格尔、马特·赫勒姆和尼克·哈里斯,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发光发亮。
这些成功的背后,是个人努力与环境支持的共同作用。
我们必须认识到,真正的平等,不是将残障群体置于“励志”标签之下,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像普通人一样,追逐梦想,勇敢前行。唯有如此,才能真正让每一个“小小的我”,拥有“大大的世界”。

